|
新型高端智库 https://itic-sci.com/gkx_dist/Informal-news/18.html 采编|心怡、韩大漠 撰文|心怡 图片|Ece 20岁,本科大四直接攻读某知名研究所博士,两个月后,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 这是Ece。 生理性别女;身份认同:非二元性别。 初次和他接触,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阿斯伯格”的清晰形象,把他当作了一种可汲取的资源,来装满我心中贴了“阿斯伯格”标签的篮子。 可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你满足不了 我心中对阿斯伯格的想象” 在和他第一次聊天的过程中,我不断问他人生中遭遇的困境,努力寻找他贴着“阿斯伯格”标签的经历,来满足我的刻板印象。 我找到以下“痕迹”—— “想要和同学处好关系,但出了问题却不知原因为何。” “尽力地去跟别人互动,但总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觉得自己在社交中呈现的是积极的态度,但在跟其他人相处中总是格格不入,别人也不会主动来跟他交流。就连出席某些活动也经常被搁置一边,他们却聚成一堆。” 一一在这些符合阿斯伯格的描述后打勾,收入囊中。 “因学业/社交各种问题产生的压力焦虑抑郁而反复多次想要去确诊,并且用药物来辅助。” “学习上,科研没有问题,所以一路升博,但对他来说困难的是人际关系。” “小时候就对图形类的东西感兴趣,在脑子里有视觉画面,觉得生物就是一个个在脑海中浮现出的图像。” “身边谱系、ADHD,非二元性别和跨性别者比较多,自己也是非二元性别者。”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鲜活的,被“具体化”的阿斯,那是除“社交障碍”“刻板行为”以外的惊喜特质。 不过转念一想,好像普通人也会这样啊... 就像抓在手里的石头突然变成了沙子从指缝中流走了一样——以为抓住了,但又没有。 Ece的衣柜,按照区域划分 黄:短袖短裤;黑:打底裤;红:抱枕枕套;蓝:背心;绿:夏季睡;黑:秋衣秋裤 兴许是担心完不成任务,我一次次见缝插针地问: “我还是不明白阿斯给你带来了什么困扰。”“在我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对于我这些略带冒犯的质疑,善良的他不厌其烦地尝试解释。 他努力配合我去回忆,终于想起了一个,刚要说,却又显得有些忐忑:“不过这个例子好像也挺普通的。” 那是他两年级时追问奶奶灯泡瓦数和亮度的关系,但奶奶是文盲,又不愿损害自己作为长辈的权威,于是含糊其辞,Ece仍然追问个不停,最后气得奶奶用手砸床,也吓坏了他,这件事给他留下了非常大的童年阴影。 Ece描述的这个回忆确实让我有所触动,但他倾力想出佐证自己是阿斯的例子,其实也只能算是生活中的小插曲罢了。 因为在一些事情上,他比“普通人”做得还要好。交流顺畅,逻辑清晰,一些情感问题也能共情。幸运的,优秀的,智力高的,善解人意的,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也映入了我的眼帘。 他真的是阿斯伯格综合人士么? 在这场填色游戏中,作为颜料盘的他是“失格”的。 或者说是无法满足我对阿斯的「贪婪」的想象。 2. 试图理解他的“述情障碍” 得到一个“开放式”的结论 第二次聊天开始时,我对他直言上次的疑惑:“上次采访,我并没有明显感觉到你作为阿斯的特质。”(Ece自己也说,有的编辑采访过他后,觉得他的文章并不好写。)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有述情障碍的人。” 述情障碍,指无法感知、识别、表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这一障碍在一般人群中出现的比例为10%,自闭症人群中的比例高达50%。但有述情障碍的人,并不一定就在谱系范围。 对“述情障碍”,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我在捕捉和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总是会让别人感觉好像有一层隔膜,很不真切。” 这确实就是我的感受。 而他的“述情障碍”,除了先天对情感的感知不那么鲜明立体,还有后天压抑的结果。 而后他又描述了几件对他影响深远的事: “可能在当时我是很痛苦的,但是在后来我的防御机制是选择遗忘和回避,这样我就不用去想当时的那些东西。” 压抑或许导致了他对情感的感知愈发弱化。那些痛苦也不是真正的遗忘,据说有时会在他梦中又“冒”出来。 不过我还是不解。他能和我流利沟通,一些情感问题也能共情,怎么就是“述情障碍”了呢? 直到他说起他10岁那年的一件事,让我明白,在某些情况下,他的社交信息处理能力是不够的,并且因此而造成的困境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ce和他的猫友 小学的时候,他听信规则。妈妈告诉他别人打你你要打回人家两下,于是当别人不小心碰到他时,他也会“回打”回去。 同时,“跟别人玩”又成了他觉得必须要遵守的另一个规则。 在上学的时候,虽然他的智商超群,成绩数一数二,但在“找朋友”这件事上却不擅长。经过一番寻觅,他找到了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小团体——班级里的倒数第一第二名。他成了另外两个女孩的小跟班。 其中一个女孩在三人集体中占主导地位。 而那个女生有偷东西的癖好,每次行动时,都会拉着他一起去店里,把偷到的小东西放在他的手里“保管”,让他塞在口袋里不要拿出来,或是出了门把那些东西分给他。 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包里,并搁置在房间一角,但不知道怎么处理,只是看着,甚至有些痛苦。 虽然Ece知道,偷东西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但他当时没有任何应对的办法,一是以前的反驳都被那个女生压制住了,二是他怕失去这个朋友。 每天,包里的东西都会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是让他痛苦的:“明天会继续这样子。” 一天,在一家新开业的两元店,那个女孩突然和他“进去看看吧”。 他高兴地想:“你终于只是进去看看了。” 没想到她变本加厉地往他身上塞各种东西。那时是初春,Ece穿了一件薄薄的毛衣,加上一件薄外套。那个女孩往Ece的毛衣里塞了10多件东西,毛衣鼓得明显,最终还是被老板发现了。老板拦住了他们,那个女孩却说:“我只是跟着他一起来的。我马上要回家了。”看到女孩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老板便把“罪魁祸首”放走了。 只留Ece一个人与老板和店员交涉。 老板一直在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让他打电话,抵押书包,赔钱。他翻遍身上各种兜儿,对老板说:“我没有钱。” “你当时有跟老板说是那个女孩往你毛衣里塞东西的吗?” 他说:“我应该是没有说这句话。当时来不及,或者说也反应不过来:‘我要是说这句话就可以洗脱自己的罪名。’或者说我当时感觉自己确实在整个事件中负有很大的责任。” 他诚实地回答他们的每一个问题,或拒绝或答应,表现得就好像一个真正的小偷那样。 唯独忘了辩解。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忍着痛苦回忆起当时的心境: “当时的环境里面存在至少十几种不同的刺激。 店铺的老板娘穿了一件十分耀目的大红色的裙子,画着浓妆,在店里走来走去,对我来说这相当于举着一块红布站在牛前面的那个效果。当然我不是那种脾气大的公牛。 店铺面积狭小,也就四五平米,充斥着廉价香水味和顾客店员的人味;店铺里面拥挤而货品繁多,各种东西摆放非常密集,还不断被人拿来拿去;老板、店员、顾客走来走去,我眼前一直有人影在晃,还有交谈的人声,非常嘈杂;店面靠近马路,有来往的车声。老板身上则有一种淡淡的烟味,还有一些口臭,他和老板娘操着外地口音说普通话,这迫使我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必须要切换到普通话模式。他们的外地口音影响了我理解他们的信息,而且他们的语速非常快,迫使我也开始加快我的语速和他们配合。 因为我的语速太快而被老板认为是咄咄逼人。提问的语速快,回答的语速也快,导致我思考的时间变短乃至于消失。前一个问题的回答过于局限,没有经过很多思考且不让他们满意,引起下一个问题他们便更加大声且凶狠地提问。 我的体力很差,当时被拦下的时候胳膊被店员一把拉住,吓了一跳。之后也一直站着,腿越来越酸,后来老板给了个破凳子,坐都坐不稳,需要努力维持平衡。但当我坐下的时候,他却说‘还好意思坐下’。 而我当时还在处理那个女孩说‘进去看看’和又拿了很多东西的信息矛盾中,脑海中也充斥着一些过往的回忆。” 我问:“那这是你自己内部的信息矛盾,感官超敏,还是述情障碍?” 我还是执着为“述情障碍”确定一个说法而努力。 但没想到他说: “都不是,就不要给这种信息冲突命名了吧。” 于是我以为了解了“述情障碍”,但又不了解了。 后来Ece的母亲铁青着脸,付了200元,把他带回了家,并发现了家中的那个包袱,毫不犹豫地扔了。 因为当时那个女孩带他去的店,大部份都是卖女孩子发饰之类的东西。 母亲把这件事和他最近习惯留长发联系了起来,并说她是因为年纪到了,爱打扮了。因此之后都不允许他留长发。每次剪去长发,他都觉得是妈妈因为那件事对他的“刑罚”。 冲突发生的时刻,他常会感到混乱: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说?是不是他说的是对的? 日后面对复杂难解的局面时,也会出现:“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我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别人的,我还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别人的,我同时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我的。” 3. 趋于自我确立 18岁以后,妈妈老了,干涉少了,他也再也没有剪过头发。摸着现在长及屁股的头发,他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他说,高中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作息规律,人际关系简单。同学们来问他题目,他总是乐于详细地解答,因此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喜欢。“除了睡眠差了点,其他都太美好了”,他说。 但是到了大学,这样的时光不复存在。 他碰到了和他经常产生矛盾的室友。曾经一次和室友吵架时,他想起室友和他的互动方式与社团里另外两个人的互动方式比较相似。于是感叹并脱口而出:“怪不得你和谁谁谁很像。” 室友突然爆怒,说:“你有病吧!” 他和室友说理,说事实,而室友希望得到他无条件的“妥协”。可能需要他撒个娇就能稍许缓和的局面愈演愈烈,两个人的沟通频道始终调和不到一块。 他也有意思地发现,和很多人的关系都会发展出这种类似的状态。 因不堪和室友的矛盾,Ece来到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位有着神经多样性背景的咨询师。建议他可以往阿斯伯格征上面去想。 根据阿斯伯格求诊互助团体的指引,他得知当时在北京地区,只有一个第六医院可以进行成人方面的诊断。但在那位医生的诊断中,父母的评价在诊断结果中占非常大的比重,而他自认为得不到父母合理又客观的评论,因此没有继续。 “因为很多父母的刻板印象就是自闭症都是小孩,没有成人。” 六院求诊行不通,Ece选择自己开出一条路,去一家就诊地图上没有的医院试试。 “幸运”的是,他确诊了。 “我就真的去了那家医院,很顺利地就确诊了。确诊的时候我还把我自己的确诊信息发布在群里,大家还庆祝了一番。” 他说,有一些求诊者,去各大医院碰壁了无数次,经历了非常多的误解。如果他们受到的挫折太多,就有可能因此放弃了求诊,并且会让自己陷入更糟糕的境地里去。 “确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问了这个令我好奇的问题。 “就是明确了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属性。更加了解自己,确认以前的一些想法和猜测是正确的。” 对于一些阿斯伯格症来说,他们看似适应了社会,但只是把表面的冲突压抑到了深层次,并表现出了抑郁,焦虑,发展出抑郁症。 确诊对Ece来说,有了一个解释,可以不用去面对自己不明原因的抑郁,而是直面阿斯伯格,做心理疏导,或去求助精神科医生。 曾有人形容,确诊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照进黑暗中的一束光。 治疗ADHD的药 4. 仍在迷雾中 但或许正走向真正的融合 虽然努力建设自我,但Ece仍感觉自我是一片迷雾,有时只能通过“情景假设”和“新场景体验”来确定触动的自己的是什么。“就像研究黑箱。” “比如我有时候实在想不清楚影响自己的因素是什么的时候,我可能会假设某因素已经明确存在的情况下,我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然后通过这些变化来研究某因素是否对当时的我起作用。 像是一个场景模拟,但不一定总是成功,多半时候都不成功。但也习惯了。能成功都是有收获,算一个从0到1的过程。” 我问他:“感觉之间没有边界的感觉,痛苦吗?” 他说:“不能全是一种痛苦吧,这也算一种活法,而且好像不好改。” 而感觉边界模糊,却也成了他之后保有自我的同时,也能接受不确定性,保持开放的优点。这一优点在他稳定了自己的核心之后日趋完善。 对于人,他一直都觉得每个人都有其美,都是值得欣赏的,即便是和他闹矛盾,现在见到都躲着的那位室友,他还是保留对她欣赏的态度。 他也力争每个人权力的平等。 下面这张是他做过的一张图: 背景蓝色是他刻意选的。 大部份神经多样性群体在各种活动中会抵触使用大面积的蓝色,但是他说,他单纯地喜欢蓝色,“虽然不会在讨厌蓝色的人面前故意用蓝色,但是讨厌蓝色的人也别想剥夺我用蓝色的权利。” 我问他处理一个新的信息时候的方式,他说: “我会依据我目前获得的信息去得出阶段性的结论,但是我会承认这些结论它的阶段性,而且认为这些结论不是不可更替的,而是可以不断改变的。 这个就和那种科学探索的方式是类似的,因为科研也是一个不断更替过去已经获得结论的过程。” 也就是——确信的是不确信,不变的是变化,标签是他也不是他 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应该如此。 我还是不了解他,但我好像比一开始的时候了解他了。 虽然我慢慢远离了我内心想象出来的“标签”,并且越来越远,但似乎离“真理”越来越近了。 我问他对一篇文章中对述情障碍的描述怎么看? 他说,原文里有这么一段他是认可的,即: “有一群人,他们无法感知、识别、表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他们无法辨识出不同的情绪,难以读懂他人的表情,也不明白造成这些情绪的诱因:另一方面,在和他人沟通时,不论发生什么,他们的表情和语气都很平静,让人感觉很冷漠。” 但他补充道,这段话还没有触及本质,特别是后半句过于笼统的总结,“事实上述情障碍人不光会过于平静,还可能过于夸张。” “心理感受到的情绪当时没办法表达出来这完全是字面的意思。当然也有小部分人会有类似的体验,但是它不能涵盖所有人的体验,每个阿斯它都很不一样。 述情障碍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它可能是一种非常综合性的体验。” 对述情障碍的理解,应该是多角度的。 最后也可以归为:“每个谱系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朴素的真理。 阿斯伯格,一个标签,一个引人窥探的神秘符号。 但对于Ece来说,可能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温柔的注解。 某些时刻,他需要这个注解,仅此而已。 点击上方 更多干预课程,戳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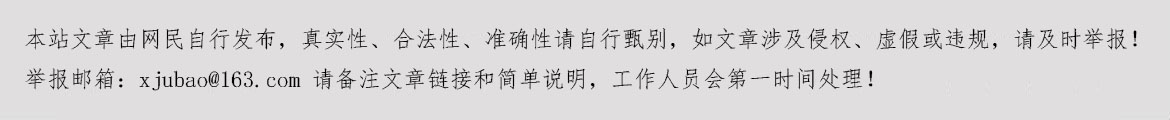
|